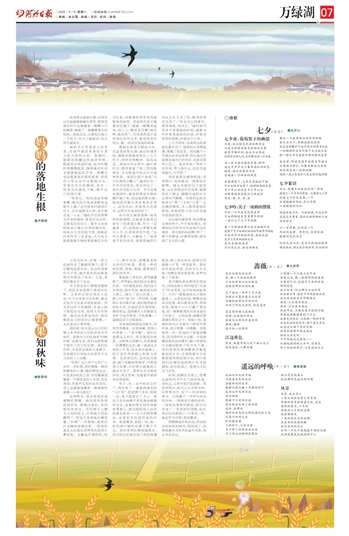■陈黎珍
立秋后的风,好像一夜之间就吹走了黏腻的暑气,把天空擦得湛蓝瓦亮。在这样清爽的日子里,城市里的柏油路显得有些辜负了秋光。于是,我想回豫东乡下走走。
车子停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,我信步走进那片熟悉的田野。玉米秆已经长得比人还高,叶子在风里沙沙作响,像是在低声交谈着丰收的秘密。阳光穿过叶子的缝隙,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,晃得人有些恍惚。就在这光影摇曳间,我仿佛看见儿时的自己猫着腰,一头扎进这片青纱帐。
那时候,秋天是从大人们的掰玉米声和孩子们的欢笑声开始的。趁着大人们在地里“咔嚓咔嚓”地掰玉米,我们这群野猴子便有了自己的乐园。我们的目标,不是那金黄的玉米棒子,而是藏在田间地头的那些不为人知的小小宝藏。
“快来!这儿有个大的!”小伙伴一声吆喝,我们便像一群闻到腥味的小猫,瞬间聚拢过去。只见垄沟的泥土里,安安静静地躺着一个圆滚滚的小东西,皮色青绿,带着西瓜似的淡色条纹,顶上还倔强地翘着一根细细的藤蔓——是马泡瓜!
这种野瓜,是玉米地里最慷慨的馈赠。遇到那些熟得恰到好处、微微泛黄的,我们便如获至宝。往往顾不上擦去上面的泥土,只用袖子胡乱蹭两下,便迫不及待地往嘴里塞。“咔嚓”一声脆响,清甜的汁水瞬间迸溅出来,一股类似黄瓜又比黄瓜更野性的清香扑鼻而来。瓜瓤是半透明的,咬一口,脆生生的,满嘴都是阳光和风的味道。那是一种淳朴的甜,直接、爽朗,就像我们那时的笑声。
要是碰上青皮的,那可就遭殃了,苦得能让我们把舌头都吐出来。可即便是青的,我们也不舍得扔,揣在兜里,跑到地头的土路上,铆足了劲儿往地上一摔,只听“嘭”的一声闷响,瓜瓤和汁水四溅开来,我们便拍着手哈哈大笑,比谁的瓜炸得更响,溅得更远,直到被大人们隔着玉米秆子高声嗔怪,才捂着嘴,一溜烟钻回了庄稼地里。
玉米地的喧闹还没散尽,风里忽然飘来一丝更细腻、更馋人的甜香——“香不榴”。我们当地都这么叫它,其实就是姑娘果。这野果长得精巧,外面裹着一层薄薄的包衣,像一盏盏没点亮的小灯笼,挂在黄豆地埂上。找它是件考验耐心和眼力的事。包衣青色的,说明还没熟透,摘下来酸涩得倒牙,可要是等它变黄,兴许明天就被别人捷足先登了。那种左右为难的纠结,现在想来,竟是童年最甜美的烦恼呢。
终于,在一丛半枯的豆秆下,我发现了一盏黄得透亮的“小灯笼”,赶紧蹲下身来,轻轻一捻,果子就落在了手心。我迫不及待地撕开那层薄如蝉翼的包衣,金黄的果实似珍珠般滚落掌心,指尖随即染上淡淡的黄色果渍——大人们曾笑着说,这是秋天给我们盖的印章。放进嘴里,轻轻一咬,蜜一样的甜汁瞬间包裹了整个舌尖。我们常常比赛谁摘得多,然后把它们装在洗干净的玻璃瓶里,晚上放在床头,盼着它们能像小灯笼一样亮起来。那淡淡的黄色果渍,在指尖久久不散,仿佛还萦绕着甜香,连梦也染上了甜意。
香不榴的甜还萦绕在唇齿间,河沟边那片我们唤作“天茄子”的龙葵果,也开始热闹起来了。它们一簇簇地挂在纤细的藤蔓上,从青涩的绿,慢慢变成深沉的紫,最后紫得发黑,黑得发亮,像谁不小心打翻了墨水瓶,把一颗颗紫黑色的星星洒在了河坡上。它的惊喜,就藏在那薄薄的果皮之下。轻轻一咬,饱满的紫色汁水便在口腔里炸裂开来,甜中带着一丝微酸。我最喜欢一把一把地捋下来塞进嘴里,因为那样吃才过瘾。只觉满嘴浆果在齿间爆开,酸中带甜的汁水瞬间驱散了秋日的干渴。我们常常吃得满嘴满手都是紫色的汁水,互相指着对方的紫脸猫笑得前仰后合,有时候我们还调皮地把那汁水当成胭脂,抹在脸蛋上,惹得大人们又气又笑。
此刻,我蹲在田埂上,仿佛还能闻到当年空气里的味道。风吹过,玉米叶依旧低语着。我忽然明白,秋天正以乡野为纸,以野果为字,写下一封深情的情书。它收藏了一声声马泡瓜的炸响,一缕缕香不榴的甜香,一抹抹龙葵果的紫痕,把它们串成了一条美丽的项链,挂在我记忆的脖颈上,只要风一吹,就会叮当作响,悠悠飘香。
我默默地对秋风说:你送的这封初秋的情书,我收到了;而那枚被岁月抚平的童年书签,我从未丢失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