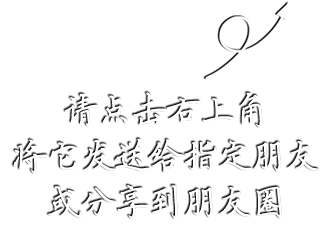■苏阅涵
初冬的第一炉火,总带着些生疏的意味。仿佛一位久别重逢的故人,乍见之下,欢喜是有的,却一时寻不到恰当的话头。那火苗起初是怯生生的,在引火的枯松针上迟疑地跳跃,舔着乌黑的炭,发出细微的噼啪声,像试探的叩问。你得耐心守着,用火钳拨弄,给它空气,也给它鼓励。直到那炭块终于被说动了心,透出隐隐的、内敛的红光,一层灰白的薄烬如轻纱般覆上,这才算成了。这时的火,便不再是客,而是这屋宇、这夜晚理所当然的主人了。
炉火一旦稳了,屋里的光景便全然改了。先前被电灯照得无所遁形的四壁,此刻都柔和下来,光影在墙上挪移,像一个沉思着的、有生命的灵魂。光是看着那火焰的形态,便能消磨许久。它时而坍缩下去,凝成一团温润的赤玉;时而又倏地蹿起几瓣焰尖,金黄而透明,活泼地舞动着,将围坐者的脸庞镀上一层暖色。人的谈话,也因为这光,不由得慢了下来。
今夜对坐的,是好友,一个沉静而富于思虑的人。我们不常谈时局琐事,说的多是些不着边际的闲话。他忽然指着炉壁上的一处光斑,说:“你看,像不像一只栖息的鸟?”我顺着看去,那光影的边缘确有些鸟羽的轮廓,随着火苗的吞吐微微颤动,仿佛随时会振翅飞去。
“这倒让我想起宋琬的一句诗来了。”我拨了拨炭火,说,“‘月去疏帘才数尺,乌鹊惊飞。’只是他那里是月光,我们这里是炉光。”
好友沉吟片刻,微微一笑:“意境却是相通的。都是那一点光影的变幻,牵动了人心深处的微澜。古人夜坐,大约也是如此,对着一点摇曳的光,便能看出一个世界来。”
这话引出了我的另一段记忆。幼时在乡下祖父家过冬,没有这般精致的铜炉,只有地上一个石块垒成的火塘。烧的是粗大的松木柴,火焰是蓬勃的、野性的,带着松脂的爆响与浓烈的香气。祖父常在火塘的灰烬里,埋上几个红薯。那等待的时辰是漫长的,孩子们围着火塘,听着屋外北风的呼号,心里却是一片安稳的焦灼。待到红薯取出,外皮焦黑,掰开了,里面是金黄糯软的瓤,滚烫的甜香混着柴火的烟气,那滋味,是此后任何精致的点心都无法比拟的。
“那不只是红薯的滋味了。”好友静静地听着,然后说,“那是整个童年冬夜的、安然的滋味。炉火之所以动人,大约就是因为它总能把一段光阴,连同那时的气味、声音与温度,一并封存起来,在往后的岁月里,时时给你温一温。”
我点头称是。我们都沉默下来,听着炉火持续的、低微的哔剥声。这声音,衬得夜更静了。我想起古人所谓的“夜气”,在这初冬的围炉之夜,体会得尤为真切。那是一种澄清的、清寒的、能涤荡白日烦虑的气息。它从窗隙门缝间丝丝透入,与屋内的暖意交锋、融合,成就了一种既不至燥热也不觉寒冷的、恰到好处的温存。
夜渐深了,壶中的水已添过几次。我们谈话的兴致,也如那炉中的炭火,由明转暗,化为了持久而恒温的余烬。说的什么,后来大抵是记不真切了,只记得那种安然与投契。起身送好友出门时,推开屋门,一股清冽的寒气扑面而来,精神为之一振。回头望去,那炉火还在原地,静静地红着,像一个信守不渝的诺言。
这一炉初火,便算是真正地接上了。往后的长夜,似乎也因此有了底气,不再那么漫长了。